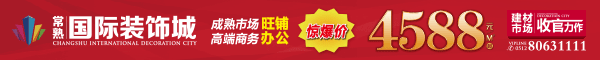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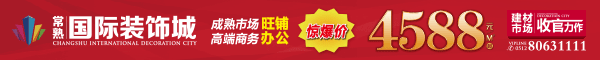

我始终觉得,在世间所有没尊严的事情中,看病没尊严是最让人痛苦的。你辛辛苦苦排队挂号,你再三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,却不曾料到,冷若冰霜的医生两分钟就把你打发走了。
坦白地讲,如今的很多医生,不仅不把病人的疾苦当回事,还不论男女,一个个跟提前进了更年期似的——脾气差也就罢了,还极没耐心。他们和病人的对话,就像“野兽”泰森全盛时期参加过的那些拳击比赛,不是以回合计算,而是以秒计算。
和那些六神无主的病人相比,我算比较幸运的,因为我至少有个靠得住的医生朋友李克。虽然我毛病不少,从强迫症、拖延症、到抑郁症,再到肠胃脆弱,动不动拉肚子,但李克总是会在适当的时候打来电话,安慰我不要紧张:“你这些都不是器官性的毛病,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”
我在纸媒工作八年,既没有因此荣华富贵,也谈不上威名远扬。但如果不是这份职业,和过去经营的那个专栏,或许我也没有机会认识李克。第一次见面,是在他的专家门诊室,当时,肝部的疼痛已经把我折磨了好几年。多疑的我甚至一度怀疑,自己是不是得了绝症。
因为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上,我偶尔有过在医院被医生拿着病历卡问“你是否就是××报的那个××”的经历。多数时候,医生也就是问问罢了。
两天后的周六,李克打来电话,约我在市中心的一家星巴克见面。见面后,他立即和我说了声抱歉,称当天外面有很多病人挂了他的号,而他又不是那种对病人敷衍了事的医生。就这样,我和李克像忘年交一样,开始了长谈,从我的文字,到我的病史,最后甚至谈到我对未来的打算。显而易见,他已经通过我写在报纸上的那些文字,对我有了八九不离十的认识。
如今的中国,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联系,要么通过关系,要么靠红包维系。但我和李克从认识到现在的这些年里,更多的是在聊电影,聊音乐,聊这个国家的医患关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虽然我偶尔也会请他吃饭,但很快,他就会带上老婆孩子,约着我和我爱人在某个餐厅见面。
某种程度上讲,李克就像是我的家庭医生。他了解我的过去,知道我有强迫症,知道我容易焦虑。自从和他认识后,我甚至很少再去医院。去医院干什么?每次面对陌生的医生,每次把自己的病史从头到尾说一遍,哪怕你没兴趣讲,而对方也没兴趣听。
毫无疑问,中国人口众多,医疗资源有限,没有太多的医生愿意去详细了解病人的过去,然而设想一下,若是中国的每个病人都像西方国家那样,拥有自己固定的家庭医生,我们是否可以少浪费些无谓的口舌,少生些莫名其妙的闷气?而医生面对自己熟悉的病人,是否也不会不好意思,动不动摆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?
在任何年代,人都会恐惧疾病。但现在的问题是,很多人不仅恐惧疾病,更恐惧去看医生。
声明:本网转发此文章,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,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、消费建议。文章事实如有疑问,请与有关方核实,文章观点非本网观点,仅供读者参考。
